白蕉《書法十講》第八講 書體(2)
作者:白蕉 書體:
(一)真書
真書,便是正楷書。今人言小楷書,便是昔人所言小真書。真、正二字,異名同實,原是通用的。初學正楷書,宜從大字入手。若從小楷入手,將來寫字,便恐不能大。昔人言小字可令展為方丈,這是說要寫得寬綽,原因是一般學者的通病,為拘歛而不開展。其實大小字的用筆、氣勢、結構是不同的,我們看看市上所流行的黃庭經放大本,對比一下便可明白,小字是不能放大的。
初學根基,為何先務正楷?為何正楷不容易學?古人頗有論列。
張懷瓘云:“夫學草行分不一二,天下老幼,悉習真書,而罕能至,其最難也。”
張敬玄云:“初學書,先學真書,此不失節也。若不先學真書,便學縱體為宗主,後卻學正體,難成矣。”
歐陽修云:“善為書者,以正楷為難,而正楷又以小字為難。”
蔡君謨云:“古之善書者,必先楷法,漸而至於行草,亦不離乎楷正。”
蘇東坡云:“真書難於飄揚,草書難於嚴重。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,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。”又曰:“真生行,行生草;真如立,行如行,草如走。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。”又曰:“書法備於正書,溢而為行、草。未能正書而能行草,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,無足道也。”
宋高宗云:“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,蓋二法不可不兼有。正則端雅莊重,結密得體,若大臣冠創,儼立廊廟。草則騰姣起鳳,振迅筆力,穎脫豪舉,終不失真。所以鍾、王輩皆以此榮名,不可不務也。”又云:“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,以八法皆備,不相附麗。至於字亦可正讀,不渝本體,蓋隸之餘風。若楷法既到,則肆筆行草間,自然於二法臻極,煥手妙體,了無闕軼。反是則流於塵俗,不入識者指目矣。”
曹勛云:“學書之法,先須楷法嚴正。”
黃希先云:“學書先務正楷,端正勻停,而後破體。”
欲工行、草,先工正楷,自是不易之道。因為行、草用筆,源出於楷正。唐代以草書得名的張旭,他的正書《郎官石柱記》,精深拔俗,正是一個好例。學真書,本人主張由隋唐人入手,其理由已在第一講談過。但唐人學書,過於論法度,其弊易流於俗。而初學書,又不能不從規矩入。那末,於得失之處,學者不可不知。茲節録姜白石論書:“唐人以書判取士,而士大夫字書,類有科舉習氣,顏魯公作《乾録字書》是其證也。矧歐、虞、顏、柳前後相望。故唐人下筆,應規入矩,無復魏、晉飄逸之氣。”
“真書以平正為善,此世俗之論,唐人之失也。古今真書之神妙,無出鍾元常,其次則王逸少。今觀二家書,皆瀟灑縱橫,何拘平正?”
“字之長短、大小、斜正、疏密,天然不齊,孰能一之?謂如東字之長,西字之短,口字之小,體字之大,朋字之斜,黨字之正,千字之疏,萬字之密。劃多者宜瘦,少者宜肥。魏、晉書法之高,良由各盡字之真態,不以私意參之耳。”
姜白石這些話,並不是高論,而是學真書的最高境界。眼高手低的清代包慎伯,他是舌燦蓮花的書評家。所論有極精妙處,也頗有玄談。他論十三行章法:“似祖攜小孫行長巷中”甚為妙喻。元代趙松雪的書法,功力極深,不愧為一代名家,其影響直到明代末年。推崇他的人,說他突過唐、宋,直接晉人。但他的最大短處,是過於平順而熟而俗,絕無俊逸之氣。又如明代人的小楷,不能說它不精,可是沒有逸韻。
我國的書法,衰於趙、董,坏於館閣。查考它的病原,總是囿於一個“法”字,所以,結果是忸怩侷促,無地自容。右軍云:“平直相似,狀如運算元。上下方整,前後齊平,便不是書,但得點劃耳。”學者由規矩入手,必須留意體勢和氣息,此等議論,不可不加注意。學者的先務真書,我常將此比作作詩作文。有才氣的,在先必務為恣肆,但恣肆的結果,總是犯規越矩。故又必須能入規矩法度。既經規矩和法度的陶鑄,而後來的恣肆,學力已到,方是真才。同樣,畫家作沒骨花卉,必須由雙鉤出身,然後落筆,胸有成竹,其輪廓部位超乎象外,得其神采,得其圜中。孫過庭云:“若思通楷則,少不如老;學成規矩,老不如少。思則老而逾妙,學乃少而可勉。勉之不已,抑有三時,時然一變,極其分矣。至如初學分布,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,務追險絕;既能險絕,復歸平正。初謂未及,中則過之,後乃通會。通會之際,人書俱老。仲尼云:‘五十知命,七十從心。’故以達夷險之情,體權變之道。亦猶謀而後動,動不失宜;時然後言,言必中理矣。”學成規矩,老不如少,初學於正楷沒有功夫,便是根基沒有打好。
 張瑞圖《行草書岳陽樓記並詩》冊 紙本 29×32厘米×20 天啟五年(16...
張瑞圖《行草書岳陽樓記並詩》冊 紙本 29×32厘米×20 天啟五年(16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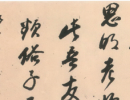 釋擔當《題思明老師像贊橫卷》,行書。釋擔當(1593-1673),俗姓唐名泰,字...
釋擔當《題思明老師像贊橫卷》,行書。釋擔當(1593-1673),俗姓唐名泰,字... 【釋文】十二月六日。告姜道等。歲忽終。感嘆情深。念汝不可徃。得去十月書。知姜等平...
【釋文】十二月六日。告姜道等。歲忽終。感嘆情深。念汝不可徃。得去十月書。知姜等平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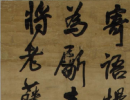 王鐸《行書杜甫戲呈楊四員外綰詩軸》綾本行書 235×54.7cm 清順治四年(...
王鐸《行書杜甫戲呈楊四員外綰詩軸》綾本行書 235×54.7cm 清順治四年(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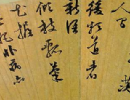 陳繼儒《行書五言詩》扇面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陳繼儒書法學習宋代蘇軾、米芾,用筆駿快...
陳繼儒《行書五言詩》扇面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陳繼儒書法學習宋代蘇軾、米芾,用筆駿快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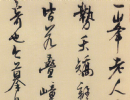 孫杕跋藍瑛《仿黃公望山水卷》,行書。
孫杕跋藍瑛《仿黃公望山水卷》,行書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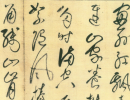 【釋文】窗外紅飄春去遲,山家養拙已多時。滿空飛絮隨風卷,一角殘山肯讓誰? 擔當。...
【釋文】窗外紅飄春去遲,山家養拙已多時。滿空飛絮隨風卷,一角殘山肯讓誰? 擔當。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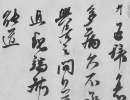 【釋文】升再拜 衰老杜門多病 久不承興居之問 日益系詠 近魏端叔見臨 能道動止之...
【釋文】升再拜 衰老杜門多病 久不承興居之問 日益系詠 近魏端叔見臨 能道動止之... 此碑又名《張景造土牛碑》。東漢延熹二年(159年)立,隸書。縱125厘米,橫54...
此碑又名《張景造土牛碑》。東漢延熹二年(159年)立,隸書。縱125厘米,橫54... 張瑞圖《岑參登總持閣五言詩軸》絹本草書 348×92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...
張瑞圖《岑參登總持閣五言詩軸》絹本草書 348×92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