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朝楷書《瘞鶴銘》
作者:不詳 書體:楷書
陶宏景隸書、行書均佳,當時他已解官歸隱道教聖地鎮江茅山華陽洞,故認為屬於他的墨跡。另一說,相傳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所書。他生平極愛養鶴,在家門口有“鵝池”。他常以池水洗筆,以鶴的優美舞姿來豐富他的書法。傳說此銘是王羲之悼念他死去的兩隻仙鶴而作。還有以為唐代王瓚、顧況所作,但均無確據、由於書法絕妙,後被人鐫刻在鎮江焦山後山的岩石上,因被雷轟崩而墜江中。至宋代淳熙年間(1174一1189)石碑露出水面,有人將它從江中撈起,仍在原處豎立起來,許多人前來觀摩摹拓,有的甚至鑿幾字帶走,學者們也來研究它,因而遠近聞名。不意數十年後,其碑又墜入江中。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由鎮江知府陳鵬年募工再度從江中撈出,粘合為一,僅存殘字九十餘個,移置焦山觀音庵。現在,在寶墨軒仍有《重立瘞鶴銘碑記》,碑記文中說到:“蓋茲銘在焦山著稱,殆千有餘年,沒於江者又七百年。”敘述了這段經過。
碑文存字雖少而氣勢宏逸,神態飛動,讀之令人回味無窮。用筆撐挺勁健,圓筆藏鋒,體法從篆隸中變化而來。結體寬博舒展,上下相銜,如仙鶴低舞,儀態大方,飄然欲仙,字如其名,表里一致,堪稱書法傑作。北宋黃庭堅認為“大字無過《瘞鶴銘》”、“其勝乃不可貌”,譽之為“大字之祖”。宋曹士冕則推崇其“筆法之妙,書家冠冕”。此碑之所以被推崇,因其為南朝時代書法氣韻,特別是篆書的中鋒用筆的滲入;加之風雨剝蝕的效果,還增強了線條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韻味。此碑的拓本及字帖久傳國際,名震海內外,是研究書法藝術之代表。它既是成熟的楷書,而又可從中領會楷書發展過程中之篆、隸筆勢遺蹤發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。
[匯品]
宋 黃庭堅:古人有言:“大字無過《瘞鶴銘》,小字莫學痴凍蠅。隨人學人成舊人,自成一家始逼真。”(《論書》)
元 劉有定:《瘞鶴銘》,題雲華陽真逸撰。在焦山之足,常為江水所沒,好事者俟水退而摹之,往往只得數句。《潤州圖經》以為王羲之書,或曰華陽真逸,顧況號也。蔡君謨曰:“《瘞鶴文》,非逸少字,東漢末多善書,惟隸最盛,至於晉、魏之分,南北差異,鍾、王楷法,為世所尚。元、魏間盡習隸法。自隋平陳,中國多以楷隸相參,《瘞鶴文》有楷隸筆,當是隋代書。”(《衍極注》)
清 馮 班:黃山谷純學《瘞鶴銘》,其用筆得於周子發,故遒健。周子發俗,山谷胸次高,故遒健而不俗。(《鈍吟書要》)
清 吳德鏇:山谷小行書自佳,蓋亦從平原、少師兩家得力,故足與坡公相輔。大字學《瘞鶴銘》,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,亦成一種習氣。學者貴於慎取,不可遂為古人所欺。(《初月樓論書隨筆》)
清 阮 元: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,是以碑碣絕少,惟帖是尚,字全變為真行草書,無復隸古遺意。即以焦山《瘞鶴銘》與萊州鄭道昭《山門》字相校,體似相近,然妍態多而古法少矣。(《北陴南帖論》)
清 包世臣:南朝遺蹟唯《鶴銘》、《石闕》二種,蕭散駿逸,殊途同歸。(《藝舟雙輯》)
清 劉熙載:《瘞鶴銘》剝蝕已甚,然存字雖少,其舉止歷落,氣體宏逸,令人味之不盡。(《藝概》)


 王頊齡跋顏真卿《祭侄文稿》,行書。
王頊齡跋顏真卿《祭侄文稿》,行書。 韓擇木《南川縣主墓誌》 唐天寶十一年(752)立,志文二十一行,滿行二十三字,楷...
韓擇木《南川縣主墓誌》 唐天寶十一年(752)立,志文二十一行,滿行二十三字,楷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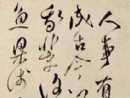 傅山草書孟浩然詩卷,紙本長卷,草書。縱28.2厘米,橫294.8厘米。此作今藏北...
傅山草書孟浩然詩卷,紙本長卷,草書。縱28.2厘米,橫294.8厘米。此作今藏北... 黃道周《鵬鳩豈有五言詩軸》 行書 1642年釋文:鵬鳩豈有常,各自喻適意。當其控...
黃道周《鵬鳩豈有五言詩軸》 行書 1642年釋文:鵬鳩豈有常,各自喻適意。當其控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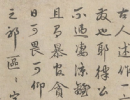 元代 鄭濤跋耶律楚材《送劉滿詩卷》,行書,至正十二年(1351年),美國紐約大都...
元代 鄭濤跋耶律楚材《送劉滿詩卷》,行書,至正十二年(1351年),美國紐約大都... 包世臣《行草書錄內史與謝尚書書軸》紙本行草書 132×55.5cm 山西省博物...
包世臣《行草書錄內史與謝尚書書軸》紙本行草書 132×55.5cm 山西省博物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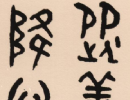 先秦人寫大篆,未經秦人精減,筆意豐富,結體多姿,還是蠻有意思的。吳大澂散氏盤集字...
先秦人寫大篆,未經秦人精減,筆意豐富,結體多姿,還是蠻有意思的。吳大澂散氏盤集字...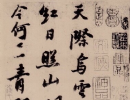 北宋 蘇軾 《天際烏雲帖》又稱《嵩陽帖》,蘇軾詩文一章,行書,真跡曾由明代項元汴...
北宋 蘇軾 《天際烏雲帖》又稱《嵩陽帖》,蘇軾詩文一章,行書,真跡曾由明代項元汴... 東晉《王丹虎墓誌》東晉《王丹虎墓誌》,志為東晉昇平三年(公元359年)刻,磚志,...
東晉《王丹虎墓誌》東晉《王丹虎墓誌》,志為東晉昇平三年(公元359年)刻,磚志,...